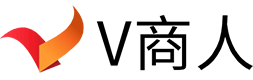如果生了病,或是觉得不舒服,你会怎么做?在今天,人们大概率会选择吃点药,若实在难受,就去医院看看。但对于中国不少乡村地区的民众而言,首先要看这病是“真病”还是“假病”。类似身子发软、寝食难安,却又说不出原因的“不对劲”,当地人的办法是先去“问一问”。生病于他们而言,不只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它影射出的可能是某种无法名状的力量,或是与人的运道有关,又或是牵扯出一段家族中的恩怨。
在江南杭嘉湖平原的九里村,当地人也是这样的看法,生(假)病了找“灵媒”,人死后去“关仙”,这些东西对于自小生活成长在这里的沈燕几乎可以说“耳濡目染”。即便她清楚,面对疾痛和死亡,人们会在许多时候生出无力感,但困惑她的是,为什么在科学日盛的今天,当地人依然保留着这种原初的信仰,“信”与“灵验”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以及这套机制又为什么会对村民们有用?硕士阶段选择民俗学后,她逐渐意识到,这背后似乎不能简单用“迷信”去解释。

不识字的奶奶们为了给儿孙拜忏准备的有名字的字牌。图片出自《假病》一书,出版社授权提供。
“你读了那么多年书,对封建迷信感兴趣?”在沈燕决定将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放在家乡的疾痛观念时,不仅是她的同龄人,甚至连当地一些村民的眼神中都透着些不解。随着研究的深入,她慢慢发现在这套疾痛观念背后,其实藏有当地人看待自己身体、看待周围世界,甚至看待整个人生的价值观念体系,这些构成了当地流传多年的地方性知识谱系。不管一个地区或国家如何发达,作为“人”所面临的身体或情感上的问题其实始终相似。
在周围人的质疑背后,也牵出了一个更为背景性的偏见。长期以来,民俗学研究常被认为是“背过身去”,朝向着过去,聚焦那些逐渐销声匿迹的奇风异俗,这些似乎连与“当下”都格格不入,更不必说现代社会所提倡的分秒必争走向“未来”了。这些是许多人在初次听到“民俗学”时会有的不解。甚至在进入民俗学专业之前,沈燕也是这么想的。诚然,民俗学史上确实发生过“民”“俗”之争,学界内部经历过一轮刮骨疗毒式的自我更新,批判了以往只见“俗”不见“人”的视角,而如今的民俗学尝试着从“俗”到“人”的转变,透过“俗”,为的是走近那些因为一不小心走得慢,而被时代落下的人。
在《假病:江南地区一个村落的疾病观念》出版之际,我们对沈燕进行了一次专访。从当年还是硕士在读的她为何想要做这样一个研究出发,我们聊到了由此引发出的民间信仰与家庭伦理间的关系,也回望当下,探察年轻人推崇的“赛博算命”与父母朋友圈转发的“养生知识”之间有怎样的相似性。九里村的研究结束后,沈燕近年来将目光聚焦于养老机构的老年群体,她也在这次采访中分享了对老年医疗中存在问题的一些思考。

《假病:江南地区一个村落的疾病观念》,沈燕著,漓江出版社,2022年4月。
上述问题意识之下,其实都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思考,借此稍微驱散些先入为主的迷障,继而从中见到“人”的身影。对于九里村的那段经历,沈燕坦言:“我只是想让更多人知道,还有一群人是这样生活的——他们的生活兼顾着生者与死者、今生与来世,他们的世界充满着洁净与污秽、神圣与世俗。在这里,一代又一代人逝去,却没有随风而逝,他们的声音仍可通过关仙婆的嘴传达出来,他们的身影仍可见于子孙后代的仪式实践中,他们的生活仍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着。”

采写 | 申璐
说起这个研究的缘起,时间还要倒回2012年3月13日,对于沈燕来说,那原本是个值得期待的日子,至少,她的母亲是期待的。那段时间,沈燕去了泰国当地的一所华人学校教中文。出国前,她的母亲就总念叨着,不想家中的这个长女离家太远,而这年的3月便是她任职期满,返程回国的时间。不过,就在预期回国前的半个月,沈燕连续好几天都觉得有些“异样”。
一天夜里,快要睡着的她忽然感觉到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遏制,她当时十分确定自己的意识是清醒的,但整个身体却无法动弹,惊慌中想要叫醒睡在隔壁床的室友,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丝毫声音。她不太记得自己那晚究竟是如何清醒过来的,但睁开眼的一瞬间,那种被掌控的无力感慢慢散去后,她只觉得筋疲力尽。室友说,隐约听到了她的哼哼声。之后的几天,沈燕接连有过两三次相似的经历。她意识到,这可能是父母一辈曾提起的“惹夜癔”,在民间的很多地方也叫“鬼压床”。
这件事情倒也并非完全无来由。当地学校附近有条狭长的过道,两侧贴有待认领的亡者的照片,待到一定时间无人认领后,这些遗体便会被拉去附近的焚尸炉火化。路过这条小道的人一般都会加快脚步。因为知道这是当地不成文的习俗,沈燕这10个月里倒也没有因此做过噩梦,但在“惹夜癔”的那几天,脑子里总会闪过些画面。她将这些事情说给了母亲听。第二天,母亲打来电话:“我去问了问,没什么事情,你回来了就好了。”

湖墩庙天井内的蜡烛山,此为过年时人们烧香的场景。图片出自《假病》一书,出版社授权提供。
母亲口中的“问一问”指的是询问村里的关仙婆。在沈燕生活长大的江南村落,当地人遇到些解释不清的事情时,都习惯去“问问”关仙婆,某种意义上,关仙婆扮演着那个连接生者世界与亡者世界的中介。尽管沈燕觉得,这些不过是母亲在借此催她回家,但这件事也促使她开始思考,当地人为何在科学日盛的今天,依然还保留着这种原初的信仰?
类似“鬼压床”这样的症状往往被当地人归为“虚病”一类,这些病症看上去无缘无故,且来得突然,当事人一般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哪里不舒服,却总是觉得身上有些“不对劲”,即便是去了医院,这些病症也总是看不好,而且还接连复发。在各类疾病被分门别类归入不同科室的今天,这些“不对劲”只得被当地人暂时称为“假病”,而“假病”自然也就有了“假病”的治法。但如今,这套疾痛观念却常常被不加分辨地笼统扫进“科学”的对立面,一句“你这些就是封建迷信”便中断了后续所有更深入的对话。
在沈燕的研究中,当地的疾痛观念指的是一套复杂的地方性知识体系,除具体的知识外,它还指从身体感受到的疼痛出发,在病因观的追寻、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当地人)生发出的看待自己身体、看待周围世界,甚至看待整个人生的价值观念体系。对于那些现代医学仍然无法解释的疾痛,村民们依据代代相传、日积月累的生活经验编织着对“不可知”的解读,同时,这些关于疾痛的解读也化作秩序的护栏,反过来维持着村民们的日常生活。
这套疾痛观念不仅与当地的人伦秩序有关,也侧面反映出村民们隐而不发的情感需求。当“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发生互动时,对病因的解释其实也是尝试为失落的情感筑起堤坝。借关仙婆之口,“家蛇”的出现或许是逝去的人在提醒活着的人不要忘记祭奠,即便没有亲缘,但当年真心实意的帮助与彼此间的扶持不要因为肉身的离世都化作云烟;一颗“仙丹”让已经被医院判了死亡的奶奶日渐好转,奶奶笑称是“小福菩萨”不想她在隔壁水仙儿子的婚事期间离世。而在奶奶去世后,母亲安慰道:“算命人说奶奶的阳寿很短,后来的寿都是延别家的,所以才生病不断。”在沈燕看来,这些其实是一种中国乡村式的“向死而生”。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乡村,接受城市现代化的洗礼,同时一并褪去昔日那些无法用于证明现代人身份的标签,可还有一批人他们仍然留在了那片土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之下是充满了磕磕碰碰的代际对话,甚至有时,一句“你别总神神叨叨”就有可能让一些话到嘴边变成了欲言又止。沈燕在书中提到一个颇为动容的细节,村上的老人总想给远在他乡的孩子求一点运气与平安,当地人称为“拜忏”,可这些老人不会写字,于是经常颤颤巍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递给庙管阿爷看,“原来在年轻一代不知道的情况下,老人们怀揣着对子女的爱,默默做了很多”,那些也许在子女看来都是些“封建迷信”的东西。

沈燕,1989年生,浙江德清人,现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法学(民俗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法学(民俗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医疗、城市老龄化。发表有《“两家并一家”之传宗接代的另类解读——阴间与阳间的连结》《灾害记忆何以传承——以一个村落地方神的变迁史为例》等文章。
病还分“真假”?
乡村疾病观下的生活秩序
新京报:在这本书中,你关注到了“假病”这个现象。当地村民有一套自有的方法去判断得的病是“真病”还是“假病”,“假病”往往来得突然,不舒服却说不清楚,而且现有的医疗手段是失效的。你提到,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人的身体观念中既包含着实体性的身体,也包含着灵性的身体,可以展开谈谈这种二元的身体观吗?
沈燕: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谈谈二元的身体观。首先是身体观本身。二元对立的身体观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在柏拉图看来,肉体禁锢着灵魂与思想,是需要克服的对象,到了笛卡尔这里,肉体与心灵则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且肉体无足轻重,心灵才是追求真理的必需。直到尼采出现,身体才得到正视,且不再是知识与真理的对立面。也是基于此,后来身体也得以进入学术话语中,包括现象学、人类学、谱系学学术传统中都有了它的身影。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学术背景,我在研究中才会关注到村民们的身体,他们被文化建构的身体以及身体实践背后的理性。这也是要谈的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回到我这个研究中。对村民们来说,其实并不存在一个二元对立的身体观,他们的身体一直是身心合一的身体。当他们生病时,他们感知到的以及去治疗的往往并非仅仅是身体或者说肉身上的疾病,而且也包含灵性上的身体,比如书中所说他们的某种身体感或者病因里提到的家族的某种失序。
所以说,通过他们的身体实践比如寻医问药的过程,可以去探究他们的逻辑,并将这种与民间信仰相关的疾病观念看作一种地方性生存智慧。衍生出去,我们也可以说,九里村村民的身体观实则反映的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身体观,即身体本就是一个整体性的身心融合的小宇宙,而且这个小宇宙还是与周围环境甚至宇宙时空融为一体的活生生的身体。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张邦彦著,光启书局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
新京报:在对“假病”病因的解释中,人们常常会借此去表达对生者的规训,或是叮嘱生者不要忘记逝者的祭日,或是转述来自家中长者的期待,比如“不要远嫁”等等,“假病”的发生实则是一个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契机,其背后似乎是一整套的家庭伦理。那么,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近似于宗教的这种民间信仰和(家庭)伦理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沈燕:首先我想说一下民间信仰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如果用西方的宗教概念来看我们的民间信仰,似乎我们的民间信仰不足以被称为宗教,比如没有独立于世俗社会与文化,没有专业化的神职人员、统一的教义等。但如果跳脱出宗教这个西方话语建构出来的学术概念,我们的民间信仰亦是一种民间宗教。
关于这一点,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反思,比如对神圣与世俗二分的反思。我比较赞同杨庆堃先生提出的“混合宗教”(也有的译为弥散性宗教)的概念或者说视角。混合宗教指的是本身没有独立理论、组织、成员,依附于世俗社会结构并成为世俗结构一部分的宗教,这也是“家国同构”的体现。
这样一来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的研究中民间宗教与家庭伦理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它们可以说是一体的。民间信仰是家庭伦理的保护机制,正是因为有民间信仰设置的奖惩规则,村民们才会如此重视家族的有序与延续,家族也才得以代代存续下来;与之相对,民间信仰也恰恰是因为根植于家族、家庭中,也才能经久不衰。
新京报:既然当地如此重视传宗接代、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那么它们有形成类似华南地区的宗族势力吗?
沈燕: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九里村明明那么重视传宗接代,却没有宗族势力,也没有祠堂。不久前我曾和一位老师聊起这个话题,不像华南地区有着明显的宗族相关的标志性文化,这个村落的宗族/家族观念其实是融于日常生活中的,比如习以为常的与信仰相关的疾病观念、年复一年的祖先祭祀,还有对阴间世界的真实想象等等。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九里村的民间信仰所包含的伦理,除了家庭、家族层面的“家庭伦理”外,也包含了整个村落层面的伦理。

过年湖墩庙烧香。图片出自《假病》一书,出版社授权提供。
新京报:对于这套疾病观念背后的鬼神信仰,信者有之,不信者亦有之,双方往往彼此无法理解,且无法说服对方。但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处于这之间的模糊地带,比如你在书中提到的你的堂哥,他们抱持的则是“信其有”,但又不愿多谈的态度。你在书中提到了一些“信”和“灵验”之间的互动,可以展开聊聊吗?
沈燕:信与灵验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讨论。其一是“信”与“灵验”之间,这两者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很难说哪个是前提,只能说它们统一于村民的身体实践中,比如有的人是先体验到了“灵验”才会去“信”,有的则是先“信”了才体验到“灵验”。这其中也就有了“信”与“灵验”之间的不对等,也就是说,“信”未必会“灵验”,“灵验”也未必只针对“信”的人,两者间也就有了很多可解释的空间,比如个体或家族的道德层面的优劣。
其二是指向“信”与“灵验”背后的人神之间的关系,重点要探讨的是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如何形成、传承下来的。人神之间其实是一种“礼尚往来”的关系。比如庙管阿爷,他们在信地方神之前都有过灵验的体验,比如生命垂危时得到过地方神的帮助,而这样的恩惠又让他们在后续的建庙事宜中担任了重要角色,随之他们又会得到地方神的格外的照顾。对其他村民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在日常实践中,在长年累月的人神交往中,建立起对神灵的信任感与真实感。

电影《吉祥如意》剧照。
朋友圈养生与赛博玄学:
人类的情感领域其实始终简单
新京报:进入信息时代,原先口传式的疾病观念逐渐被新的形式所替代。不知道你是否关注父辈一代在朋友圈大量转发的“养生类”文章。正如此前即便鬼神之说等被子女们斥之为迷信,父母们还是会“偷偷去问”一样,如今,子女们也常常用“相信科学”等劝说上一辈。在两代人的观念隔阂之外,还有什么阻碍着彼此间的沟通与理解?
沈燕:我确实有关注到父母辈们在朋友圈大量转发的“养生类”文章,还包括他们在抖音看到的一些“养生类”视频。子女在看到这些时,通常是反感、排斥的。与之相对,子女则往往想给父母普及一些他们看到的科学知识,尝试去转变父母的观念。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行为的本质是一样的,一方面是对自己认可的知识的确信,另一方面是想要为对方好的这种心理。然而两代人却出现了隔阂,这里的隔阂,我想和两代人各自的成长背景有关,比如在小孩的抚养过程中,年轻一代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间就会出现一些矛盾,比如卫生方面的冲突。
那么回到成长背景这一点上来说,年轻一代父母从小接受学校教育,是科学知识训练下的卫生观,而他们的父母一代,很多都没怎么上过学,他们知识多是来自身体实践的默会知识。而在科学知识这一话语权威下,随着时间累积起来的经验不再是长辈们宝贵的财富,甚至现在还出现了很多年轻一代反过来教授长辈知识的反哺行为。其实这里面是不同类型的“知识”之争,一面是科学知识,一面是经验智慧。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而要让两代人之间实现顺利沟通,我想唯有彼此间的体谅与包容。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实践起来其实很难。所谓体谅与包容,是要放下已有的偏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比如当父母转发养生类信息时,与其反感或说教,不如尝试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关注这类信息,为什么觉得它有道理,是否与他们过去或当下的经历相关等等。基于此,原本可能引发彼此矛盾的行为也会成为理解彼此的契机。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尽管年轻一代在努力划清与祖辈父辈在疾病、甚至是所谓的“迷信”之间的界限,但面对未知的“命运”时,体内那种与前人相似的敬畏又会复苏。近年来,不论是星座、塔罗,还是MBTI等各类测试已然成为年轻人当中热议的话题,这些被戏称为“赛博玄学”或者说“赛博算命”,你会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沈燕:我一直觉得许烺光先生在《驱逐捣蛋者》一书里提出的观点很有道理。他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即使是在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人类的情感领域也始终是简单的,它包含的内容并不多,爱、恨、怒、喜、绝望、希望、焦虑、忍耐、宽容、忠诚等等,而且即便在时间的长河里有所变化,那也是微乎其微的。

《驱逐捣蛋者》,许烺光著,南天书局,1997年。
同时他也认为,人们推崇的新年和活动多属于情感范畴,我们的情感模式最终决定了我们选择做什么,由此美国人倾向于接受科学并以科学的外衣来包装魔法,而西城人和沙田人(许烺光的田野调查地)倾向于接受魔法,用魔法来解释科学。另外,他也明确指出,宗教与科学是人类需要的双胞胎。因为人类总会面临生老病死以及各种情感问题,还有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等,而这些并非仅仅依靠科技就可以解决。
你提到的星座、塔罗或者各性格测试等,事实上也是年轻人在应对生命无常时很自然的反应,当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无法帮他们解决问题时,他们也需要去寻求另一种解决方式,哪怕他们获得的只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或心灵上的慰藉。而且,其实除了你提到的这些西方的方式,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找算命先生、风水先生,也会去一些据说很灵验的寺庙烧香拜佛。所以重要的不是形式或名称,而是他们内心真实的需求特别是情感需求,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的。
新京报:近年来,相较于原先人们对死亡的“避讳”,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与生死相关的讨论。类似《寻梦环游记》等影视作品的热播似乎为“死亡”这一严肃的议题蒙上了一层相对温情的面纱,这背后暗含了不同文化语境中怎样的生死观?
沈燕:《寻梦环游记》这部电影出来时,我注意到很多人都被电影里那种浪漫的生死观所感动,比如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真正的死亡是不再有人记得你,还有生死之间依旧可以沟通,在某些特殊的时间空间两者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等等。但我列举的这些,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也有,比如祖先崇拜及其祭祀仪式,还有葬礼,传达出来的也是这样一些观念。关于死亡,我们也建构了一个亡灵的彼岸世界,以及生死之间的沟通方式,只是它们好像越来越容易为我们所遗忘。
遗忘的原因很复杂,比如现代性家居空间、城市空间的变化,我们的时间观念的变化,还有葬仪的现代性改革等。当然也有人会觉得,我们中国人在面对死亡时往往是非常严肃、凝重的,特别是当其与孝道结合在一起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民间的一些葬礼其实也有狂欢的一面,比如有的地方会击鼓而歌。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文化中也不乏对死亡的美好、浪漫想象,而像《寻梦环游记》这样优秀的外国影片,也是我们反观自己文化的非常好的契机。有意思的是,墨西哥亡灵节最初是墨西哥古印第安人的节日,而有学者认为最初的印第安人可能与古代中国有着诸多联系,如果基于此再来看两者在生死观上的某些相似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电影《寻梦环游记》剧照。
做老年研究,
首先要看得见老年人
新京报:在完成九里村的田野调查后,你又相继去了上海一家养老机构和老年互助会,研究兴趣也从以空间为中心的社群疾痛观念转向了以时间为中心的老年人群的疾痛叙事,硕士期间的那段九里村田野经历对你后来的研究道路有怎样的影响?
沈燕:九里村的田野经历对我来说主要有两点影响。第一,它让我关注到了老年人这个群体。因为田野中遇到了很多老人,他们的老年困境包括身体上的疾痛以及精神上的生命意义感的丧失,这些都让我不自觉地想要去关注这个弱势的边缘群体。同时,跟他们的相处经历也有助于我后来在养老机构调研时与其他老人的交往。
第二,它也让我认识到跨学科研究的魅力。这里的跨学科主要指民俗学与医学人类学。民俗学给予了我接地气的与研究对象平等交流的视角,医学人类学又给了我很多研究理论方面的启发,这两者的结合把我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都囊括了进来,包括疾病、衰老、死亡,而且让这些研究都成为可能。
新京报:插一个题外话,很多初涉研究的学生常常困惑于找不到自己的研究兴趣,缺乏问题意识,又或者不知道具体从何去切入一个研究选题,作为青年学者,可以分享一些经验吗?
沈燕:经验实在谈不上,我本身也还只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学者,所以只能就自己的经历谈一点想法,未必正确。
我个人觉得学术研究中有很重要的三点。其一是在问题意识方面,最好是找寻跟自己或身边的亲朋好友密切相关的话题及问题,这种从实际生活当中生发出来的问题意识会让你在研究中始终保有探索的动力,而且从生活中生发出来的问题往往才是真问题。
其二是认识到学术研究本就是一件有趣又痛苦的事。有趣在于探索的过程,从查阅文献到田野调查,不断去尝试寻找各种答案来回应一个问题,这是很有意思的。但同时研究中也会遇到一些困境,比如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拒绝访谈,还有不断去梳理逻辑甚至推翻之前的想法等,这些都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孤独、烦躁与无助。
其三是认识到个人及学术研究的有限性。特别是当我们想要去回应一个比较难的社会问题时,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都能体验到人类本身的有限性,比如在面对死亡时,而在这种时候除了要承认并接受自己的“无能”外,也要学会去调整状态,回到做这个研究的初心上来,回到接地气的问题意识中来。其实我个人觉得,学术研究并非是外在于研究者的一个课题或一份工作,而是始终与自我紧密相关的探寻生命意义的人生事业。

破旧的围墙和肆意生长的竹子。图片出自《假病》一书,出版社授权提供。
新京报:说回老年医疗,在最近出版的《银发世代》中,作者路易斯·阿伦森观察到在美国的医学界内外,普遍存在对老年群体的偏见与怠惰,医院往往更加关注如何延长老年人的寿命,重大疾病一般被置于优先级,而像虚弱、疼痛这些对老年人至关重要的体验,大多数医生其实并不感兴趣。更不用说那些就连患者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假病”了。据你的观察,国内有类似的问题吗?你在养老机构做田野调查时有哪些发现?
沈燕:是的,我在养老机构做调研时也曾发现类似的情况。比如有的老人觉得身体不舒服,养老机构里的医生做了基础检查后,比如血压血糖都是好的,再加上送医院需要子女同意,那有的子女就不会在意,认为老人只是在“做”,由此老人也就无法外出就医。这也是为什么有的老人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了或者说觉得进了机构就是在等死了的原因之一。而要外出就医,往往是在出现明显生理症状或有明确疾病,不得不去医院的情况下,比如晕倒、发烧、咳嗽、呕吐、牙疼等等。
但我这里谈的只是我在养老机构看到的现象,并非是在医院。不过我也遇到过有的老人即便身体不舒服也不愿去医院就医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旦进了医院就要进行各种检查,检查项目繁多,花钱不少,一番折腾之后也没什么用。但这也是老年人的一个视角,我不太确定现在国内的医院是如何按照疾病来对老人进行区别对待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研究一下。

《银发世代》, [美]路易斯·阿伦森著,中信·24HOURS | 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7月。
新京报:随着老年人口的持续增长,出现了一系列围绕老年群体的衍生概念,比如“银发经济”等,而在这些以老年人之名的提法中,(日常生活中作为个体的)老年人又处于怎样的位置?
沈燕:就以“银发经济”为例吧,其实这中间有很多值得琢磨的地方。其中涉及到一个“社会医疗化”的问题。简单来说,社会医疗化就是通过医学来控制日常生活领域,包括生老病死等各个方面的医学化。从老年领域来说,比如衰老变成了一种可以延缓甚至治疗的疾病,死亡也变成了一种可选择的可控的结果,基于此,寿命的延长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随之而来的还有这样一种观念,即个体需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负责,因为健康是人为管理出来的,而当个体成为主要负责人时,相应的市场需求也就应运而生了,想来这也是各种养生类信息及保健产品如此盛行的原因之一。一些疾病被创造出来,一些需求被创造出来,医学话语就成了控制市场、控制人的工具。
只见“俗”不见“人”:
民俗学如何与当下社会问题接轨?
新京报:中国民间的医疗观念笼统而言属于民俗的范畴。然而环顾我们的舆论环境,民俗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时而被指认为一种经验式的总结,无可避免地陷入迷信的窠臼,时而又被大肆鼓吹,贴上博大精深以至无所不能的标签。结合你的田野经历,你觉得外界对民俗研究存在哪些误解?
沈燕:民俗包括民俗学本身确实常常被人误解。有的人是通过我做的研究认识我,但当他们得知我的专业是民俗学时,(他们)都会非常诧异。我想这种诧异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种误解。他们觉得,民俗学应该就是研究传统文化或奇风异俗的,它是朝向过去而非面向当下、或朝向未来的。事实上这也是我在学民俗学这个专业前的想法。
这种常见的误解,和民俗学本身的发展历史也是相关的。民俗学学术史上有过“民”“俗”之争,对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都进行过探讨,批判了以往只见“俗”不见“人”的研究路径,简而言之,民俗研究经历了由研究“俗”到研究“人”的转变。也是基于此,现在的民俗学才可以与当下的社会问题接轨,以平视的姿态,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
此外,我想这种误解也和传媒时代民俗专家的频繁出镜相关,因为他们出镜的时间或是在某些传统节日,又或是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场景中,由此也就加强了民俗学与过去、传统的关联,以及你说的这种“博大精深”的标签。说到这里,其实我觉得另一个问题更值得重视。我在九里村田野调查时发现,很多民众作为民俗的传承者,他们对自己所持有的地方文化没有自豪感,甚至认为那是封建迷信。在地方文化中,他们是失声的。就像在一些非遗中,很多原本真正的非遗传承人被湮没一样。当外界的、专家的声音大于局内人或当地人的声音时,这一现象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湖墩庙里的求签筒。图片出自《假病》一书,出版社授权提供。
新京报: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在研究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疾病时,曾提出“躯体化”的概念,认为中国人惯用身体化的术语来表达个人和社会的痛苦,导致疾病可能会成为社会问题的隐喻。你在书中表示了对这一观点的怀疑,可以具体谈谈你的考虑吗?
沈燕:首先我声明,我本人其实非常赞同,也很喜欢“躯体化”这个概念。它让我们看到身体的生成性、复杂性,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表达背后可能隐藏的深意。我想这都是他者视角才更容易看到的问题。
至于我对这一观点的怀疑,其实是源于我自己在研究时遇到的困境。这个概念自然也可以用在我的研究中,村民们的疾痛叙事背后自然有很多社会问题的隐喻,比如他们在中老年时期常见的腰酸背痛,跟他们长年来机械式的重复的体力劳动紧密相关,再比如村落里愈加常见的癌症,许是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有关。但是除此之外,我更想看到村民们的主体性,他们如何解释自己的疾痛,又如何去应对这些疾痛。
事实上他们并非不知道自己身体遭受的苦难背后的社会根源,只是很多时候他们无力解决,而当这种无力成为日常,那他们又该如何在这种日常里继续带着希望生活下去?也是因为通过他们的这种主体性视角,我的研究才最终将九里村的疾病观念呈现为了一套地方性知识体系。受此启发,田野调查期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捕捉到较为完整的日常生活,而非仅仅是片段式的疾痛叙事。只有沉浸式地生活在当地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才有可能看到真正的社会文化建构下的疾病的各个方面,继而获得一个较为系统性的理解与阐释。如果说“躯体化”是让身体隐身,让位于社会问题,那么我的研究应该是尝试重新把身体调回前台,让它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疾痛的故事》, [美]凯博文著,方筱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2月。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贯穿整个研究,我注意到你在不断重申,上述这些常常被当代人归入“迷信”的鬼神观念背后,其实是某一地域内人们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生存智慧,值得正视与思考。不过,你会担心一旦矫枉过正,这种“正视”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吗?
沈燕:其实之前也有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觉得我好像是在为封建迷信代言。不过,我个人不太会有这种矫枉过正的担心。
首先这一现象本就是存在的,它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中传承下来的,是世世代代的村民们自主选择的结果,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左右的。其次我这里的“正视”一方面指学术研究下的“正视”,另一方面是针对那些一概漠视,特别是鄙视这些“封建迷信”的人来说的。对我来说,我的正视就是尝试去理解并写下村民们的所思所想,呈现出他们真实的生活日常。我没有宣扬也没有贬低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不过我承认可能因为我是局内人,里面提到的很多人都是我的亲人,所以会带有情感地去描写一些场景。但同时我也在书里提到了我内心的理性与感性之争。
此外,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其实科学知识和生存智慧并不对等,我们不能以科学知识的眼光来批判生存智慧,而是应该尝试将之放到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去理解它存在的逻辑,而理解也并不意味着认同,更多的是一种尊重。

电影《寻梦环游记》剧照。
新京报: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之中的“度”的问题?
沈燕:这就要看这个“度”指的是哪方面的度了。如果说是信这种“封建迷信”的度,那我其实没有权力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村民们有自己的度,包括我和同村的同龄人们也有自己的度,而村民们的度和我们的度,都是在各自的身体实践中体悟出来的,而且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和神灵之间的礼尚往来的过程。
如果指的是学术研究中的或者作为一个局外人在面对这些现象时的“度”,那我觉得首先还是理解与尊重吧,但如果接下来发现和自己的价值观相冲突,那就还是应该尽量去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就像我和同村的同龄人一样,出于理性的不信,出于感性的信,然后在两者间寻找一个让长辈和让自己都相对满意的动态平衡点。
最后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星座、塔罗的问题上,这是当下很多年轻人会玩的或信的神秘学。但这里也有一个“度”的问题,不少人虽然觉得它们准,但也不是尽信。我想这种“度”其实和村民们的信仰态度是一样的。虽然有人诟病中国人的民间信仰的不纯粹,觉得这种信仰太过功利,但我反而觉得恰恰是这种对实用性的追求,这种“度”的来回跳跃,呈现出了一种游戏人生的轻松诙谐姿态,而这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申璐;编辑:青青子;校对:贾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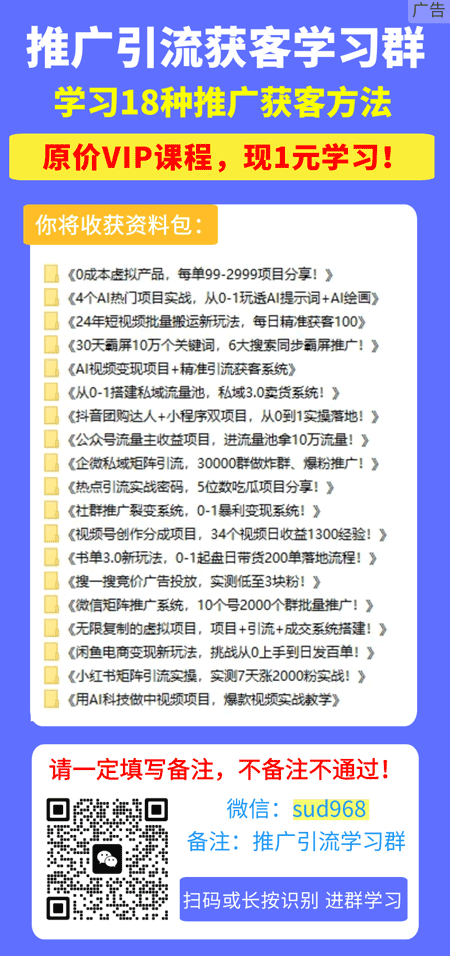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vsaren.com/123821.html